男女主角分别是沈如晏沈韶光的其他类型小说《韶光不误无删减+无广告》,由网络作家“AAA菜市张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她是花满楼最红的清倌人,人人说她痴情。他是寒门书生,一朝高中,娶了贵女,弃了她。她借他银子,他借她名声;她助他登科,他娶了权贵嫡女,转身便断前缘。长安城初夏,浮云卷了青天,落日将一地青石街烧得泛红。街角的香饼铺子前排了长队,吵嚷声夹着炊烟缭绕,一张张面孔在光影里交错。沈韶光站在队尾,低垂眼睫,静得如一道剪影。她站得极稳,像一株在风中微微摇曳的香草,楚楚,却不弱。她身边不远,是忠勇侯府嫡女沈如晏,随行三名丫鬟,才下香车,正笑着与铺中老板讨价。沈韶光轻轻抬眼,那一瞬,像一柄绣着云纹的刀,藏锋而现。“姑娘前日的金铃耳坠可还在?”她轻声一句,仿佛无意搭话。沈如晏回眸,眉眼带着教养出来的温婉与距离:“姑娘认错人了。”“不会认错。”沈韶光微笑,...
《韶光不误无删减+无广告》精彩片段
她是花满楼最红的清倌人,人人说她痴情。
他是寒门书生,一朝高中,娶了贵女,弃了她。
她借他银子,他借她名声;她助他登科,他娶了权贵嫡女,转身便断前缘。
长安城初夏,浮云卷了青天,落日将一地青石街烧得泛红。
街角的香饼铺子前排了长队,吵嚷声夹着炊烟缭绕,一张张面孔在光影里交错。
沈韶光站在队尾,低垂眼睫,静得如一道剪影。
她站得极稳,像一株在风中微微摇曳的香草,楚楚,却不弱。
她身边不远,是忠勇侯府嫡女沈如晏,随行三名丫鬟,才下香车,正笑着与铺中老板讨价。
沈韶光轻轻抬眼,那一瞬,像一柄绣着云纹的刀,藏锋而现。
“姑娘前日的金铃耳坠可还在?”
她轻声一句,仿佛无意搭话。
沈如晏回眸,眉眼带着教养出来的温婉与距离:“姑娘认错人了。”
“不会认错。”
沈韶光微笑,像春水漾起,语调却冷得极稳:“那日你在菱花巷,挑了一对镶金铃,与你随行的……应是新科探花郎顾清越吧?”
那一瞬,沈如晏知面前之人非等闲。
沈如晏问:“姑娘有何事?”
沈韶光将那油纸包递上前,语声低却极稳:“这一包香饼,是他最爱吃的那种。
我从江南带来,算是个见面礼。”
“姑娘到底是谁?”
她敛下眸光:“花满楼,沈韶光。”
空气凝住。
沈如晏听说过这名字。
顾清越入京后,曾被“花满楼”的头牌助力金银,传为美谈。
如今不过三月,他便披红骑马,迎娶她这个侯府嫡女。
这世道,总爱看寒门中第与清倌恩情交缠的“佳话”。
只是这佳话听多了,她只觉得腻。
夜落长安,灯火如昼。
沈如晏抬手,递出手中三物:一纸赎身契,一张宅契,一份田契。
沈韶光坐在侯府的偏厅里,喝完最后一口茶,将茶盏轻轻搁下,说:“沈小姐出手不俗。”
沈如晏语气平平:“比起他从你身上取走的,我这点,只算添头。”
沈韶光勾唇,“他从我这拿走的,是我主动给的。”
沈如晏抬眉:“哦?”
“他以为我痴情,我就顺势装给他看;他想攀附门第,我就替他铺路。”
“他不爱我,我不爱他。
他用我谋前途,我借他换自由。”
她说得轻巧,像聊一场旧戏。
沈如晏沉默片刻
,忽然轻笑。
翌日忠勇侯府前,金碧辉煌,灯花已点。
沈如晏站在正厅前“沈韶光之身,已是自由人。”
账房跪地:“小姐,此举……恐惹闲话。”
人言可畏?
侯府怕这个?”
她淡声一笑,“那她当年拿钱供他进京时,又有谁替她遮羞?”
“再说,今日本就无喜可言,退婚,正合我意。”
迎亲队伍抵达侯府门前。
鼓乐戛然而止,门匾未启。
门前侍卫冷声通禀:“探花郎顾清越到。”
片刻。
府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一线,一名老管家躬身行礼,却不请他入内。
只呈上一封亲启信函。
顾清越打开,熟悉的字体入目——是沈如晏的字。
“婚约之事,自此作废。”
“侯府不嫁负信之人。”
“余赎沈韶光之身,清账断情,各不相欠。”
“你我此生,勿再相见。”
他怔在原地,脑中思绪千转。
四周百姓议论声起:“这是……被退婚了?”
“探花郎那清倌佳话,原来不是佳话,是戏文?”
“说到底,靠女子供着的寒门郎,再好也难登大雅之堂。”
红绸如火,喧哗渐止。
顾清越站在原地。
他以为自己计算得极准——中举、娶贵女、进仕途,一步步完美无缺。
他以为沈韶光柔弱、沈如晏善良,皆可温和应对。
他从没想过,这两个女人,会一刀断他路。
数日后。
教坊司批文下达:沈韶光脱籍,转为良民。
坊间哗然,清倌脱身本就难得,更何况她还得了侯府田宅赠契,自此立户为“韶氏”。
沈韶光离京。
不告别,不回头。
她坐在车中,揭开帘子,看见远处官道边有一个衣衫破旧的小姑娘,正被巡兵撵走。
她让车夫停下,从车上丢出一只小包袱,里头是几文铜钱和两块饼。
小姑娘扑过去,磕了三个头。
沈韶光没说话,只垂眸淡淡看她。
她从前也是这样的小姑娘。
没人救,只能自己救自己。
车轮滚滚向南,驶向江南昭州。
她没爱过顾清越,没盼过谁救她,她从头到尾只信一个道理:“凭自己,才能活得漂亮。”
同日,东宫。
太子萧止言站在回廊中,月色映他一身雪衣,手里那封退婚折子仍未收起。
他没问缘由,只道一句:“她终于肯看清了。”
皇后轻声道:“你要娶她?
她刚退婚,风声正紧。”
萧止言望着那方冷月
,语气却极轻:“她不是退婚,她是在弃一根烂绳。”
“我不怕世人说她清冷无情。
我喜欢的,就是她这种干脆。”
三日后,朝堂上传一道奏折:“探花顾清越,因自请归乡任地方职,朝廷准。”
顾清越那日回乡,未带妻未带礼,带着一身空回的讥讽。
其实早在那日他踏入花满楼,看到沈韶光向他递来茶水时,他就知道她不是为情来。
她笑着说:“你若高中,赎我如何?”
他说:“你若助我,我便为你赎身。”
他们都知那是戏词。
她借他起名气,铺人脉,铺银子铺香饼;他借她之手入勋贵圈,走捷径入门第。
一个要自由,一个要权柄。
情从未在棋盘上。
沈如晏?
更不是。
她是忠勇侯的嫡女,是他通往朝堂的一座桥。
他没爱过她,也没指望她爱他。
只是可惜——桥塌了。
顾清越不怒不惧,只是将三份文书叠整齐,拂拭干净墨角,对身旁旧仆吩咐:“准备车马,我要出京。”
“回乡。”
他轻声。
江南接他的旧友问:“你怎么回来了?”
他只说:“功名不稳,婚事有变。”
没人再提他和侯府的“佳话”。
因为那佳话,一夜之间碎得干净。
昭州,盛夏。
清风拂过,荷花开了一整河。
沈韶光立在“昭光社”门前,衣袂轻拂,背后是一道雕着凤纹的红漆门匾,金字熠熠:昭光。
取意“明昭天下,赐光女子”。
她今日身穿藕荷色直襟褙子,手执一卷账册,立在晨风中,眸光平稳清亮。
管事来报:“姑娘,第一批人选到了,三十七人,八成是被休的,剩下是弃儿、落籍女、逃亡丫鬟。”
“技艺呢?”
“会针线的九人,识字的五人,其余全是白板。”
“白板好。”
沈韶光淡淡道,“白板才好落字。”
她走进讲堂,众女齐跪,望着她的眼神或惧、或仰、或迷茫。
她望了一圈,声音稳而不响,却字字敲在耳边:“我不收可怜人,我也不是菩萨。”
“你们来昭光社,不是求恩的,是来学本事的。”
“在这里,你们要记住一件事——没有人能救你们,包括我。”
“我能给你们的是一条活法,能不能活,是你们自己的事。”
她一字一句讲完,落座执笔,在昭光社的社规本上写下第一行:昭光社 开堂规不求良配
,不嫁权门,不念旧情,不入侯门。
立身凭技,谋生靠己。
笔锋入纸那刻,全场静默。
同一日,昭州府衙。
顾清越身着青色官袍,立于卷案前,翻阅的是一摞江南水政旧档。
他已任职三日,查封私盐两处,整顿粮商六家,罚没银一万两。
府衙的老吏私下议论:新来的顾大人,手段狠、准、快,不留情面,也不结交官场任何门路。
“他不像想升迁的。”
“不,他比谁都想升,只是不靠人情。”
顾清越此刻却在看一封书信。
信是清流派某主事所递——朝中清流派打算在南地扶植一批寒门基层官,为来日朝局争一席之地。
顾清越在那信尾,写了一句回信:“我顾某,自不靠侯门,亦不屑攀贵族。”
“然若清流要动江山,我必为开渠之水。”
他合起信纸,抬头望向窗外,笑了一下,声音极轻:“果然还是我赢了。”
她要自由,他转弯给了她;她要断,他不追她;她以为她下了局,殊不知他早转身另布棋盘。
<“天下女子想翻身,靠的终究不是自己,而是天下换了王。”
黄昏,昭光社。
沈韶光收到了一封信。
落款不是顾清越,是一封江南州府函件,内容却简单:“顾大人建议清查各地不良户籍制度,建议部分良善贱籍女子重归良籍,赋身份、给田契。”
沈韶光淡淡一笑:“无爱无恨,唯有争锋。”
“若他说服清流替女子改籍,我便引女子入书堂,教她们识字读律、管账书信。”
“他动权,我养人。”
她将信收起,转身看着窗外,桃花落尽。
她再提笔,在“昭光社”社规最后一页,写下第二条新律:女社成员可读书、可经商、可议政、可自组下社。
她要的不仅是自救,而是让千万人不必再求救。
大婚前三夜,太子府无灯宴,无贺客,只有风声穿堂。
萧止言坐在暖阁内,一盏茶未动,眼前是一封赐婚圣旨,盖着皇帝亲印,朱红艳艳,盖住了一切流言蜚语。
沈如晏进门时,他还未抬头。
“陛下让你入宫问安?”
“宫里传出来……圣体又重了。”
沈如晏在他对面坐下,动作如常,不施粉黛,眼尾却透出疲惫。
她没有问“你为何还娶我”。
她只道:“你可知,这场婚,我退了他,朝堂说我势利
;我嫁了你,说我谋宫。”
“世人嘴贱,不如你心狠。”
萧止言终于开口,嗓音冷得像山间的雪,“你退婚那日,我便知你这心,不会为谁跳。”
“可我偏喜欢这样的人。”
沈如晏笑了。
“太子殿下,情话说得挺冷的。”
“我不是说情话。”
他认真地看着她,“我是在说——你是我选的后,也是我爱的女人。”
她抬眼。
萧止言继续道:“我从十三岁识你,就知道你能做东宫之主。”
“我这一生,不贪情,也不求妾。
我要的是一个能和我并肩,坐得稳凤位、护得住名节、管得住后宫的正妃。”
“你,是我唯一能信的。”
沈如晏沉默一瞬,然后起身:“那便成婚罢。”
“三日后,我做你的王妃,也做你的人。”
萧止言轻轻一笑:“我信你。”
皇宫,皇帝病榻之上,气若游丝,太医跪成一排,却都低着头,不敢言“无救”。
而枕边,只有一张拟好的圣旨:“太子即日起权摄六部,入内阁听政。”
天子将病,局势必动。
昭州,昭光社分堂开设第三日。
沈韶光看着眼前这批新入社的女子,一眼扫过,有个身影令她略停片刻。
那是一个贵妇打扮的中年女子,衣着虽旧,却眉眼极端稳重,不卑不亢。
“此人姓霍,曾是侯府妾室,被休,带着一女一仆逃来昭州。”
“她原是良籍,家中却无力接济;愿以十年绣艺,换昭光社一个身份。”
沈韶光没说话,只淡淡吩咐:“收下。
安置在女艺房,但不得教书,先看三月。”
她行事从来谨慎——哪怕对方看似无害,也要先看本事再言地位。
同日,顾清越坐镇水政衙门内。
下属呈上一份密函:“顾大人,世家贵族议会有人联名反对‘女子户籍新编制’,称此制‘破礼制,乱纲常’。”
顾清越看了一眼,便搁下:“他们怕的,不是女子翻身,是自己的女儿有了选择。”
下属苦笑:“但这事若闹大,陛下病重,太子刚权摄六部,此时出风头,恐为不智。”
顾清越冷静道:“我不挑战世家,但我要尽地方之责。”
“让女子得名册、得户口、得可用的绣艺之地,不是造反,是尽职。”
“告诉清流诸公——我的动作,不越界,不越矩。
但也不退。”
他淡淡补一句:“如果怕得
罪人,那就别出来做官。”
京中,东宫沈如晏收到了“昭光社分社”的名册抄录,一页一页翻着,最后停在那个名为“霍氏”的名字上。
“霍氏……”她想了片刻,道:“去查这是否是永安侯府那桩‘妾谋主位案’中,被牵连的妾妇。”
贴身婢女迟疑:“若真是,她入昭光社意欲何为?”
沈如晏眼底清寒如雪:“若她只想活命,昭光是庇护所;若她要复仇,那就是刀了。”
“我想看看,沈韶光要怎么接。”
昭州府衙东厅内,顾清越站在廊下,望着新送来的《女籍开编试行案》。
他亲自主持这份制度三月,试点只一州,如今却因一件事被推上风口浪尖。
昭光社分社收容了一名“永安侯旧妾”,身份复杂,被贵妇圈联名上折弹劾。
说白了,是世家贵族圈子坐不住了。
“她若是贱籍,没人说话;她是贵族出身,哪怕被休、被打、被逐……也没人允许她进‘那种地方’。”
“那种地方”,指的就是昭光社。
顾清越手握卷宗,面色不动。
他的幕僚低声问:“顾大人,是否要下令清退?”
顾清越淡淡道:“昭光社非官属,乃民间自立。”
“若有人违法,法办;若制度出错,我改。
但若因身份被驱,那不是法,是私怨。”
“我顾清越,不干这种事。”
与此同时,昭光社主堂沈韶光坐在堂前,众女一排跪地,她眼前就是那位“霍氏”。
“霍氏,你知为何唤你?”
霍氏抬头,眼圈发红,却跪得极稳:“奴知身份不清,惹来非议。
愿即刻离社,免姑娘为难。”
沈韶光看她一眼。
“你在我这儿,是良籍、有技艺、有律书证的绣女。”
“我只问你一句:你可曾偷、骗、伤人?”
“未曾。”
“可曾借社谋事?”
“未曾。”
沈韶光点头。
“那你回女艺房,按原工养。
谁敢驱你,先问我答不答应。”
此话一出,底下轻微哗然。
她站起身,声音平静如水,却带着冷意:“我设昭光,不为争朝堂,只为给你们一口饭吃、一处可活。”
“但若世人觉得连口饭也得挑门第分出身,那我,沈韶光,先不答应。”
她从来不过界,但这一次,她主动下场——为的不是一个霍氏,而是她千百个姐妹未来的身份。
京中,皇城御书房。
沈如
晏披着宫衣坐在案边,正在阅折。
一封加急密信由东宫送来,内容是:“顾清越不肯驱逐昭光社‘贵女’,曰制度不能因门第废人。”
沈如晏看完,只淡淡一笑。
贴身嬷嬷道:“娘娘,此事太子若知,怕是要起疑。”
“不会。”
沈如晏轻声道,“他若真疑顾清越,早就下旨拔了他的位置。”
“他没动,是因为顾清越懂分寸。”
她顿了顿,眸光落向窗外,月色清寒如洗。
“这局棋,已经走到最后几步了。”
“顾清越守正,沈韶光走心,太子掌局。
三方不交锋,却都在对峙。”
“谁先动,谁就失了先机。”
嬷嬷低声问:“那娘娘……打算做什么?”
沈如晏笑意极轻,却说了八个字:“不动如山,坐看风起。”
暮春惊雷夜,雨未至,雷先响。
昭光社分社传出一桩惨事:一名年仅十五的女学员上吊自尽,遗书残字潦草,只留一句:“我不愿再回家。”
世家贵族圈第一时间散播谣言:“此女为忠仁伯府庶出,入社三月后口出大逆之言,拒不回门。”
“乃是女社怂恿鼓动,离经叛道。”
“如今自尽,正是因其被女社蛊惑,毁了教养、毁了名节。”
一天之内,整个南地震动。
“女社毁女”迅速登上舆论顶端,接连几州发文弹劾,矛头直指——沈韶光、昭光社、顾清越。
昭州太守衙门,紧急议会。
顾清越站在中厅,手执案卷,目光如刀。
礼部副使已将折子传回京城,内阁四名清流大臣联名表示:“若顾清越不止女社之乱,恐生变数。”
知州欲言又止:“顾大人……太子已在途中。
他若问,您如何应答?”
顾清越缓缓抬头:“我无罪可认。”
“女社未教乱法,未驱抗命。
一个姑娘死了,该问罪的是逼她回去的家族,不是让她活下去的社。”
他声音不高,却压住一室。
沈韶光穿过雨夜,亲自入后院探看。
少女的尸体已被接走,只剩她枕下那封被撕毁的书信——残页上一句话清晰刺眼:“社主说过,我们可以活,但我已经太晚。”
她站在堂前,衣襟半湿,缓缓坐下,一字不落地读完那纸遗书的残稿。
“姑娘,是不是我们错了?”
沈韶光没有抬头。
她只是冷冷道一句:“我们不是神,只是让她们多一个选择。”
她抬头看天:“是她生得太晚,不是我们给得太早。”
三日后,太子入昭州,召集公开问责议。
场上云集三方:昭光社三名执事、顾清越、礼部使臣、太子监正亲临。
厅堂百官围坐,昭州百姓围于堂外,雷雨将至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太子翻阅文书,忽抬眼问:“顾清越——你主张女社制度、推动良籍女子新编,若此事真系女社所致,如何处?”
顾清越沉声答:“若女社鼓动叛法,我亲自关门;若女社为女子留命,我绝不斩手。”
此话一出,堂上几人倒抽冷气。
太子眼神如刀:“你这是逼本宫选边?”
顾清越抬眸直视:“殿下若要清我,只需赐纸笔,我自引颈伏案,不言一字。”
众官震动。
太子却未动,只将手中文书合起:“我还未要你死,顾卿别急。”
厅堂沉寂。
这时,殿外忽有人报:“社主沈韶光,欲入堂自辩。”
太子眼色微变。
“让她进。”
沈韶光入堂,雨衣未脱,浑身冷意,跪在中厅。
她举头,目如刀锋,开口便道:“那名死去的姑娘,亦姓沈。”
众人一惊。
她抬手呈上一封信,盖有忠仁伯府私章。
“她逃出京时,曾写信求我收她入社。
她不是被诱,是来逃命。”
“她死,不是因社,而是因为她曾回府,被活活打了两日。”
全场寂静。
她眼神笃定:“此事,我不辩女社清白,我只问一句——死去的,是不是人?”
“若她是人,那社,就是让人活的地方。”
“若她不是,那天下千万人女子,该归何处?”
此言落,厅外百姓爆出低声抽泣。
堂上礼部副使额上冷汗,太子合手:“此案停审,先彻查伯府。”
他看向顾清越,声冷如霜:“顾卿,昭光之案,本宫给你三日。”
他再看向沈韶光,语气不缓:“昭光社三月内不得再扩,不得再招新。”
“你若再出事,昭光之名,必灭。”
沈韶光叩首,答得极轻:“昭光不为争,是为留。”
“若天不容,那我一人担。”
夜,太子归营。
沈如晏站在帘后,听完全过程,一言未发。
太子看她:“你若今日说一句‘女社该灭’,我就诛了她。”
沈如晏轻声回一句:“你诛得了她,却诛不了千千万万跟她一样的女子。”
“陛下病重,南地不稳。
你选一
个,是女人死,还是局乱?”
太子沉默半晌,缓缓吐出一句:“本宫,不选人,只选天下。”
雨终于落下。
昭州泥泞,街道泥水翻涌。
但女社门前灯火未灭,顾清越案前笔未停,沈如晏夜里一语未出。
元和十九年,又一年初夏。
皇帝崩逝,萧止言登基,年号改元“承道”。
五月大赦,太后诏令清理旧籍,赦良女贱册之名;同年秋,朝廷正式设立“昭光社学”制度试点,限女子教授经艺、女红、理计,入编地方学馆。
不称官职,不设秩禄,却得“可开堂、可授人、可申冤”。
这一年,被记作——女子启教元年。
昭州东南,旧昭光社址。
院门已换新匾,改名为“昭社学塾”,收生百人,皆良籍女子。
主事非他人,正是霍氏。
她曾是落魄贵妇,今为南地女子教习,女社三年,她成了“女子可师”的活榜样。
而沈韶光——不见踪影。
据说那日昭光社正式归官,她亲手卸下门匾,封存社章,留下一句话:“昭光之名,至此为止。”
她未登京,也未得赏。
只是有人说,江南湖畔新开一茶馆,主人姓沈,擅调香,偶尔教字。
承道元年,秋高气爽。
顾清越任中书左丞,掌吏部与户部联席,三年清政,被称为“寒门入阁第一人”。
他进谏开女学,减冗官,归编制,不逾矩不乱政,三年之内,不收外财,不结党派。
太后感其清直,特赐一匾:“一线清风”。
他曾婉拒宰相之位,只道:“臣做官,不为封侯,不为传名。”
“只愿所立之法,百年后仍存。”
皇城未央宫。
沈如晏为中宫皇后,十年不立妃。
她不干政,却治后宫如治国,六宫不争,礼仪肃然。
国史记载:“承道元年,后为政本、女教设籍,首倡家训、家礼、女师,不言功,实则法源。”
她一生不曾自称功臣,只在册文末题下一句:“愿我之所立,女后之所依。”
江南湖畔,沈韶光,立于茶馆之外,种梅。
她不再称“社主”,不再上朝,但每月初一,仍收南来北往女学书信,亲笔回复。
有稚女问她:“夫子,你后悔不做官吗?”
她笑着回一句:“做官太累,讲理太慢,我宁愿讲书。”
“讲什么书?”
她看着院中千枝新梅,道:“讲一讲女子该如何自处
,如何立身,如何能撑得起自己的一世。”
夜,顾清越至。
他已四年未见她,如今立于这间旧茶馆,像旧人踏入新梦。
她给他斟一盏茶。
“你变了。”
她轻声。
他笑:“你也是。”
她问:“你登阁了,后悔当年昭光之事吗?”
他答:“若为前途,不该扶你;若为民命,不该不扶。”
“如今看来,不扶你,我不甘心;扶了你,我也不悔。”
她没说话,只叹息一声:“可惜,我从未要你扶。”
他低头:“我知。
所以你走了。”
她微笑。
“如今这样,我教得书,种得茶,我就知,我对了。”
顾清越静静看着她。
良久,只低声道:“你对了,亦赢了,叫我输得心甘。”
宫中,沈如晏夜梦惊醒。
她坐起身,心头极静,窗外新月如钩。
她唤侍女:“今日,昭光初立十年。”
“我想去宫外走一趟。”
白纸之上,人各落笔,笔锋不同,余音皆在。
谁也未称王,谁也未封神。
可那些开口说要活得明白、活得漂亮的人,都走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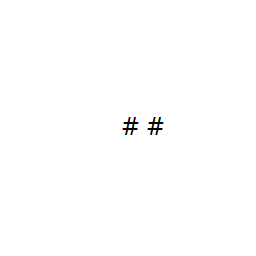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