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陈丽华张翠芳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九寨沟的蓝陈丽华张翠芳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s月白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我盯着绿幕前那排粉色衣衫,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犯人临刑前要穿鲜艳衣裳——好让血迹不那么刺眼。
《九寨沟的蓝陈丽华张翠芳全文》精彩片段
我盯着绿幕前那排粉色衣衫,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犯人临刑前要穿鲜艳衣裳——好让血迹不那么刺眼。
然出现在取景框边缘,她手心里攥着那支被没收的玫红口红,
市代码。
清新剂,
时,发现陈丽华右手无名指有圈白印——那里本该有枚婚戒。
陈丽华把九寨沟旅行团的宣传单贴在养老院公告栏上,用粉色荧光笔圈出“仅限健康状况良好者报名”。
我站在人群最后,听见她刻意提高音量:“周叔,您最近血压不稳定,还是留在院里参加插花课吧。”
插花课——上周她刚用热熔胶枪把所有人的作品固定在泡沫板上,说是“防止搬运时散落”。
我翻开体检报告,指着医生潦草写下的“心肺功能正常”几个字:“我比张伯强,他上周还忘吃降压药。”
张伯正巧路过,拄着拐杖的手抖了抖:“我、我没忘!
是陈主任说新药要饭后吃……”陈丽华的笑容僵在脸上,像一张没贴好的面膜。
她低头在平板上划了几下,调出我的档案:“您女儿特意嘱咐,说您去年体检有轻微心律不齐。”
我盯着她屏幕上小满的聊天记录,最后一条是昨天发的:“爸要是闹,就说我不放心。”
后面跟着三个拥抱的表情,虚伪得像超市促销送的免费试吃品。
“行。”
我把宣传单折成纸飞机,朝窗外一掷,“那我自己去。”
纸飞机撞在“最美夕阳红”展板上,扎进张阿姨假笑的脸。
陈丽华的瞳孔缩了缩,像猫看到猎物逃脱时的本能反应。
当晚,我的房门被敲响。
周阿姨站在外面,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:“我儿子帮我报了名,但医生说我的肾……不适合长途。”
她声音很轻,像怕吵醒走廊监控摄像头,“你要用我的名额吗?”
我还没回答,陈丽华的影子就从拐角处漫过来,灯光把她的身形拉得很长,像一把缓缓出鞘的刀。
“周阿姨,”她甜腻腻地开口,“您儿子刚来电话,说旅行团改成家庭套餐了,他陪您去。”
周阿姨的手指蜷了蜷,报名表上的“家属陪同”四个字被她的汗水晕开,像一滴没忍住的眼泪。
旅游大巴停在第一个观景台时,陈丽华像幼儿园老师一样拍手集合:“各位叔叔阿姨,我们先拍集体照!”
她从背包里掏出折叠支架,动作熟练得像在组装医疗器械。
老人们被安排成三排,前排坐轮椅,中间站着的按身高排序,后排的必须举起养老院发的蓝色遮阳帽——据说是为了“画面色彩协调
”。
我站在队伍边缘,看着周阿姨被安排在正中间,像个人形展品。
她的笑容很标准,嘴角弧度刚好露出八颗牙齿,和陈丽华培训课上示范的一模一样。
“周叔,您往中间靠靠。”
陈丽华指挥着,手里的平板已经调出拍照模式,“家属们等着看呢。”
我往后退了一步,后背抵上景区告示牌。
金属边框硌得肩胛骨生疼,上面写着“禁止跨越护栏”。
“要不您帮我们拍?”
我把机械相机递过去。
陈丽华没接。
她的视线在我和周阿姨之间扫了个来回,突然笑了:“也行。”
她接过相机,动作生硬得像在握手术刀,然后——“咔嚓。”
“好了。”
她把相机还给我,屏幕上显示着一张模糊的集体照。
老人们像被泼了水的油画,面容融化在刺眼的阳光里,只有陈丽华自己站在画面最前方,笑容清晰得刺眼。
“哎呀,手抖了。”
她毫无歉意地说,“还是用我的手机拍吧,有自动修图功能。”
第二次集合拍照时,我提前调好了相机参数。
陈丽华指挥大家喊“茄子”,我却在快门按下的瞬间,故意晃了晃手腕。
照片洗出来时,所有人都模糊成一片色块,像被雨水打湿的水彩画。
只有角落里的周阿姨是清晰的——她没看镜头,正伸手抚摸一棵古树的树皮,皱纹与树纹交错,像两种不同形式的年轮。
“重拍!”
陈丽华的声音拔高了八度,“这怎么发给家属?”
老人们面面相觑,张伯小声嘀咕:“我觉得挺好啊,比我儿子P的那些真实……”陈丽华夺过我的相机,手指在按键上胡乱按着,像在给不听话的机器做心肺复苏。
翻到下一张照片时,她的动作突然停住。
那是我偷拍的——她低头整理药箱时,一缕头发从耳后滑落,疲惫的眉头皱成“川”字,和平日里精心维持的完美形象截然不同。
她的指甲在相机外壳上刮出刺耳的声音:“周叔,您到底想干什么?”
“拍点真的东西。”
我指了指她手里的相机,“就像这张——你看起来终于像个活人了。”
傍晚自由活动时,我在栈道上遇见周阿姨。
她站在观景台边缘,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明信片。
风把她的白发吹得蓬乱,像团将熄未熄的火焰。
我举起相机,她突然回头:
“别拍。”
声音很轻,但很坚决。
我放下相机,她犹豫了一会儿,把明信片递过来。
上面是二十年前的九寨沟风景,背面写着一行字:“等病好了,我们再来。”
字迹已经褪色,但那个“病”字被反复描过,笔画深得像刻进纸里。
“我丈夫写的。”
她笑了笑,眼角皱纹堆叠,“他没能等到第二次化疗结束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,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旧照片——妻子站在同样的位置,蓝围巾被风吹起,像道愈合中的伤口。
周阿姨的指尖在照片边缘轻轻擦过,突然怔住:“这个构图……”她快步走到观景台栏杆旁,站定,回头,阳光穿过她的白发,在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那一瞬间,她和照片里的妻子重叠了。
回到酒店那晚,我发现房门把手上的头发丝不见了。
出发前,我特意在门缝夹了一根自己的白发——现在它没了,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。
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闪着红光,像只永不闭上的眼睛。
我假装弯腰系鞋带,瞥见陈丽华的影子从安全通道的门缝里漏出来,又迅速缩回去。
半夜,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动静。
睁开眼,月光把陈丽华的轮廓投在墙上——她正俯身翻我的背包,动作熟练得像在查房。
我的相机被她拿在手里,她对着窗外的路灯检查胶卷剩余数,橘色口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
我故意翻了个身,床垫弹簧发出刺耳的呻吟。
她的背影僵住了,但没回头。
“找安眠药?”
我哑着嗓子问,“在左边口袋。”
她终于转过身,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听诊器:“周叔,您睡前心率有点快。”
“被你吓的。”
她没接话,把相机放回桌上时,金属外壳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
走到门口,她又停下:“明天去长海,海拔高,您最好……最好别乱跑,别乱拍,别给组织添麻烦。”
我替她说完,“知道了,陈主任。”
门关上后,我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备用胶卷——今天下午在景区小摊买的,过期三年,包装上落满灰尘。
长海的栈道窄得像独木桥,护栏锈迹斑斑,底下是三十米深的冰川湖泊。
老人们被勒令排成一列,像串被绑在一起的蚂蚱。
陈丽华走在最前面,每隔五分钟就回头清点人数,手里的平板电脑记录
着每个人的实时心率。
我在拐角处停下。
这里视野最好——湖水蓝得发黑,倒映着雪山,像块被岁月打磨过的老玻璃。
我举起相机,后退两步调整构图,鞋跟碰到松动的木板。
“周叔!”
陈丽华的声音刺破空气。
她冲过来拽我的胳膊,指甲陷进皮肉里:“您不要命了?!”
老人们齐刷刷回头,张伯的助听器发出尖锐的啸叫。
“我在拍照。”
我挣开她的手,“又不是跳湖。”
“拍照?”
她冷笑,指着警示牌上“禁止攀爬”的图标,“您觉得家属看到这种照片会怎么想?”
“会想我终于做了点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她的胸口剧烈起伏,平板电脑上的心率曲线此刻飙成一座陡峭的山峰。
突然,她夺过我的相机,镜头对准自己:“拍啊!
拍我!
看看您女儿会不会满意这种‘作品’!”
取景框里,她的脸扭曲着,橘色口红晕出唇线,像幅被雨水淋湿的油画。
我按下快门。
咔嚓。
她愣住了。
“这张不错。”
我收回相机,“终于有点像人了。”
回程的大巴上,周阿姨悄悄坐到我旁边。
她手里织着一条深蓝色围巾,毛线针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某种密码。
“陈主任让我看着您。”
她头也不抬地说,“说您再乱跑,下次就取消所有外出活动。”
我望向车前排——陈丽华正低头翻看今天的照片,指尖在屏幕上划得飞快,像在搜寻什么罪证。
“那你现在算卧底?”
毛线针停顿了一秒。
“我儿子和陈主任是同事。”
她声音很轻,“在民政局社会事务科。”
我猛地转头看她。
阳光透过车窗,在她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。
她终于抬起头,眼角皱纹里藏着某种我熟悉的东西——那是妻子最后几个月常有的神情,一种温柔的决绝。
“所以您明天……”她递来一团毛线,“能帮我缠线吗?
就在湖边。”
我接过毛线,触感柔软得像握住一只垂死鸟的羽毛。
余光里,陈丽华正盯着我们,手里的矿泉水瓶被捏得咔咔作响。
最后一卷胶卷拍完时,陈丽华拦住了回房间的路。
“需要检查内容。”
她伸出手,腕表上的心率监测器闪着绿光,“确保没有危险画面。”
走廊灯光惨白,把她影子拉得很长,像道横亘在地上的裂缝。
“什么算
危险?”
我把相机护在胸前,“拍你算吗?”
她嘴角抽了抽:“比如悬崖、深水、或者……或者老人真实的皱纹?”
僵持中,周阿姨的房门开了。
她端着水杯经过我们身边,突然踉跄了一下——温水泼在陈丽华的白大褂上,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。
“对不起!”
周阿姨慌忙掏纸巾,“我帮您……”趁这空隙,我迅速拧开相机后盖,抽出最上面那张胶卷藏进袖口——那是今早在湖边拍的,周阿姨站在晨光里,白发像团燃烧殆尽的火焰。
陈丽华反应过来时,我已经把剩余胶卷递过去:“慢慢检查。”
她对着灯光一张张查看,眉头越皱越紧——全是空镜头:天空、树影、被风吹皱的湖面,没有一张人脸。
“满意了?”
她狐疑地打量我,突然伸手拽我袖子。
胶卷从袖口滑出半截,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——周阿姨的杯子再次“不小心”翻了。
这次是整杯咖啡。
深褐色的液体在地毯上蔓延,像片正在干涸的血迹。
陈丽华的白球鞋被浸透,她终于尖叫出声。
我弯腰“帮忙”时,胶卷无声地消失在厚重的羊毛地毯缝隙里。
抬头正对上窗玻璃——倒影中,周阿姨冲我眨了眨眼,像个刚恶作剧成功的少女。
暴雨来临前的夜晚,陈丽华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她手里拿着我的相机,指节发白,像是攥着什么罪证。
“周叔,”她的声音比平时低,像是被雨水浸透的纸,“我们需要谈谈。”
她翻开相机的后盖,里面是空的——胶卷已经被我取出,藏在床垫下。
但她没有质问,只是把相机递给我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
那是我妻子五年前在九寨沟拍的最后一组照片中的一张——她站在珍珠滩瀑布前,蓝围巾被风吹起,像一道愈合中的伤口。
照片右下角有一小块空白,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
“这张照片,”陈丽华盯着我,“您每次拍风景,都会在同样的位置留白。”
我沉默。
她翻开相册,里面全是我的“废片”——模糊的树影、虚焦的湖面、被风吹散的云。
但在每一张的角落,都有一块刻意留出的空白。
“您不是在拍风景,”她说,“您是在等她入镜。”
窗外的雷声滚过,像是天空被撕开一道口子。
陈丽
华没有没收我的相机。
她只是坐在床边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旧照片的边缘,像是触摸一道早已愈合的疤痕。
“我父亲也是摄影师,”她突然说,“他最后一张照片,拍的是医院的窗帘。”
我抬头看她。
她的橘色口红已经斑驳,露出原本苍白的唇色。
“他肝癌晚期,疼得拿不稳相机,但还是坚持要拍。”
她扯了扯嘴角,“他说,得让照片记住他最后的样子,而不是那些P过的遗照。”
我盯着她腕表上的心率监测器,数字跳得很快。
“您知道吗?”
她轻声说,“我删掉的那些‘违规照片’,其实都备份了。”
她从手机里调出一张——阿尔茨海默症的赵爷爷,只有在镜头对准他时,才会停止颤抖。
“我以为控制镜头就能控制风险,”她苦笑,“但有些东西……根本控制不了。”
凌晨三点,陈丽华把相机还给了我。
“胶卷在抽屉里,”她说,“我没看。”
我拉开抽屉,里面是那卷被她“没收”的胶片,封口完好。
“为什么?”
我问。
她站在门口,背影被走廊的应急灯拉得很长。
“因为明天要下暴雨,”她头也不回地说,“而您应该有机会……拍完那组照片。”
早餐时,周阿姨没来。
服务员说她一早就去了湖边。
我在栈道上找到她时,她正对着湖水梳头,白发披散,像一片将融未融的雪。
“我丈夫是舞蹈演员,”她突然说,“他走之前,说想再看我跳一次。”
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。
“可我再也没跳过。”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节目单——上面印着她年轻时演出的剧照,身姿舒展,像只振翅的鹤。
“您昨天拍的照片,”她看向我,“能给我一张吗?”
我递给她一张——晨光中的她,白发被风吹起,指尖微微抬起,像是即将起舞的姿势。
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,然后轻声说:“够了。”
暴雨来得比预报的更早。
我们被困在山间小亭里,雨水像瀑布一样砸在屋顶上。
陈丽华本能地掏出平板,要组织“安全报备合影”。
老人们没人动。
张伯的助听器在雷声中发出刺耳的嗡鸣,李姨紧紧攥着那支断掉的口红。
陈丽华的手指悬在屏幕上,迟迟没按下拍摄键。
我举起相机:“要不要试试……拍点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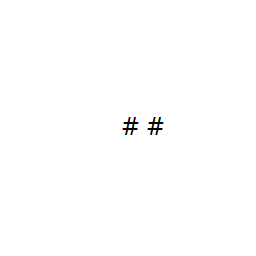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